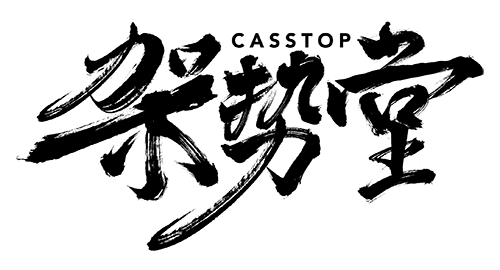“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这是曾经的“追风少年”高旗的理想。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乐的巅峰时期。他的声望与地位,与唐朝和黑豹不相上下。
现在,他依然酷,依然率性,但是他成熟了。他开始执著于为他们那个时代拍摄纪录片,开始反思他们当年的本能驱使,更不得不去想未来的自己的路怎么走。
当他终于再次发布新作品的时候,他似乎回望得有些远,远到几乎看不见“摇滚”:为经典的五首宋词谱曲并组织童声合唱团演唱。不过高旗却是从宋词里看到了他们那拨人当年的影子:“因为在官场上没有地位,所以他就不忿儿,然后他还自有一番对生活深刻的认知、豁达的态度,他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也不装,也不刻意端着,但是自然而然就站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角度。”
其实,这位当年重金属歌手已经有了新的高度:他还想着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推动群众文化的发展,满足更多人对音乐的需求,例如—他老爸的老年合唱团。

高旗
“就是玩儿”
高旗说其实他小时候从来没背过诗词,更不是想要赶最近被《中国诗词大会》等文艺节目推起来的诗词热潮,因为《宋词辑壹》的创作早在五六年前就开始了。那是为了什么呢?有三个字在采访过程中他说了好几次:“就是玩!”
儿时的高旗对宋词虽然并不感兴趣,不过他知道那是歌词,算是古时候的流行歌词,既然后来干了音乐这一行,又擅长写旋律,于是这个想法有一天就突然蹦了出来:“这个词牌它原来的旋律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前的人们是怎么把它唱出来的?这是个挺好玩的事,我可以试试!”
高旗把给宋词谱曲的过程形容为“像破案一样”,在创作时他一直不断揣想当初文人雅士云集一堂听歌女演唱这些词章时的情境。
“像柳永那些词人,换到今天他其实就是摇滚明星。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很牛,另外当时的人也像追星一样追他们,能唱他一首词就感觉特别骄傲。在我心目中,他们的形象就是那种特别酷的。现在说起宋词啊文学啊多么高雅,但他们当时肯定没这么想。首先因为在官场上没有地位,所以他就不忿儿,然后他还自有一番对生活深刻的认知、豁达的态度,他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也不装,也不刻意端着,但是自然而然就站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角度。他牛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像今天我们崇拜鲍勃·迪伦或披头士一样,所以给他们的词写旋律,你也要用一种特别酷的态度才行。”
人们一般把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在高旗看来这也都是毫无必要的条条框框。“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吧,之前大家可能都是一听 大江东去 ,就要吼起来了,我就觉得根本用不着这样。所谓豪放和婉约也是后人分的,我不信苏轼、辛弃疾他们当时就把自己放在豪放派里了。而且我发现当你把一个像这样比较沉重的词还原成优美的旋律,听起来反而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我给《念奴娇·赤壁怀古》写的旋律就非常委婉,但我觉得它比那些吼的能更深入骨髓,因为这样你才能听出来在词人藏在豪放下面的那些对于生命无常的感慨,更刻骨铭心。”
“不是给宋词赋予时代感”
对于自己的创作,高旗很有信心。虽然之前也早有音乐人给宋词谱曲演唱的先例,比如邓丽君和王菲都演唱过的根据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改编的《但愿人长久》,但高旗觉得那个感觉不对,从歌词的编排到旋律到整个表达的味道都显得太现代。
“我更想要做的是还原,而不是给宋词赋予什么时代感。对同样的一阕词,10个音乐家会有10种理解,我只是把我理解的讲出来。当然也可能我的也不对,宋朝那时候唱的不是这个样子,那没关系,至少我觉得目前我这个应该是最贴近原始面貌的。”后来高旗还专门去做过研究,搜寻到一些现在能找到的宋代的工尺谱,他自信地笑言:“那些旋律倒确实是有浓浓的宋朝味儿,但是我觉得我写的更好听。”
既然只是为了好玩,高旗便没有太当回事,从几年前把这些宋词的旋律写出来后就放在那儿没再管,之后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觉得不错,鼓励他应该拿去制作发表。“听了朋友们的话,我自己再去听听,也发现那感觉真是不一样。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干这事之前从没背过一首词,主要背不下来,记忆力不好,但是写完以后发现自然就全会背了。因为这些词当它不是念而是唱出来以后,就更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个画面瞬间就出现在眼前,像长出翅膀一样,飞进你心里去了。”
孩子唱出来,更质朴更直接
决定了要发表,但是应该用什么方式将其呈现出来,又让高旗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找流行歌手来唱,他认为唱不出那个味儿。正好高旗的父亲高伟是资深的合唱指挥,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的艺术顾问,他建议高旗采用童声合唱,高旗一听觉得很靠谱。
“这个宋词如果让成年人来表达,他就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之赋予太多的个人色彩,而孩子什么都不想,就是把旋律唱出来,更质朴更直接。而且宋词都不长,以我们今天的欣赏习惯,一首歌一分钟就唱完了那肯定不行,但如果是合唱的话,我就可以做出交织的声部,让它有更多层次和丰富的变化。”
和李健的合作也是出于高旗父亲的建议,高旗说两人的合作很顺畅,他把歌曲小样发过去,李健很快回复“挺好听的,那行,我唱吧”。录制时偶尔两人会交流探讨一下“这个方向行不行”之类,也都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梦想、童声合唱团与群众文化
做这样的专辑,高旗认为很有意义。“就像我说的,这个诗词小时候背不下来,唱出来就很容易背会了,那现在孩子都要背这个,如果你把这些歌推广进学校、课堂,让大家都好背,不就是一件功德嘛。再说我会作曲,这算是老天赐予我的天赋,它在给你这个才能的同时也就给了你一个使命,你要把它传播出去,我想这是我在这个世间该干的事。人活一辈子最后总得留下点什么,如果这些旋律光是留在我的脑子里、硬盘里,那是没意义的,我得要把它制作出来。”
另外高旗还有一个梦想,希望由此能组成一个优秀的童声合唱团,到世界各地去演出、拿奖,因为全世界范围很少有几个童声合唱团是唱原创作品的,而他已经制作完成和还在计划中的宋词作品却足够支撑合唱团开专场音乐会的,这样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来自中国古代的这些美妙词句。
还有合唱本身也是对音乐一个最好的启蒙训练,很适合于推动群众文化的发展,高旗说他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目前国内有很多合唱团,尤其各种中老年的、业余的合唱团,也需要有更多好的曲目。讲到这里他笑着说:“所以我爸现在老抢我的歌,有的我还没录完呢,他一看 嗯,这个不错,先给我们唱吧 ,就抢过去给他的老年合唱团了。”
成熟以后,反思当年的“本能驱使”
高旗把宋代的大词人和今天的摇滚明星画上了等号,认为他们豪放不羁,率性而为,“特别酷”,那么作为一位摇滚明星,高旗自己当然也少不了这种“特别酷”的特质,比如沉寂多年后突然甩出一张看似和摇滚毫不搭边的宋词专辑。而他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另一件大事明显也是出于此种性格特质,那就是做一部关于中国摇滚乐的纪录片。这些年淡出乐坛,没有出新歌也很少接演出,正是为了专心做这件事,还都是自掏腰包亲力亲为。
高旗从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进行采访拍摄工作了,至今已采访过圈内几十位重要人物,积累了数百个小时的影像素材,只是受制于资金困难,所以现在还未能制作完成。谈到拍纪录片的初衷时,他说是想给中国摇滚乐和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份记录。
“对于当时的各种事有很多以讹传讹的传闻,而我们自己就是身在其中、创造历史的人,应该把它尽可能最贴近真实地记录下来。而且当我们在做那些事的时候其实挺盲目的,只是内心的本能驱使你做这件事情,不清楚自己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就是做了,写了那些音乐,有了那些举动。当成熟以后,反过来再看,才会明白。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当回头反思你20多岁的时候,你对人生的认识就会更上一层,这时候你再去审阅你的人生,能更清晰地把它的脉络表现出来。”
拍摄的过程让高旗觉得乐在其中,因为和那些共同在音乐中成长起来的老朋友们聊天,大家的观点出奇地一致,彼此有很多认同感,也都是最放松、最真实的状态,“一路收获了很多心灵的互动和感动”。然而高旗之前没想到片子的后期剪辑还需要那么多的经费,这让他捉襟见肘,拖拖拉拉做了很久,现在也还是经常要面临停滞不前的困境。不过高旗没有想过放弃,他表示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片子做完。“如今再回头看80年代、90年代,再回来讲这些故事,不仅是高度的还原,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内心的历程,把人生里特别好、特别酷的东西分享给今天的人,同时也让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的人有一个反思,想想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
“不用看别人的脸色”,90年代的追求
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至少高旗已经想好了。相对于如今一片唱衰的声音,他对中国摇滚反而充满信心。
“我从不认为摇滚乐在走下坡路,我觉得摇滚乐的路一直走得特别对,而且新的这一代摇滚乐队都特别好。我听过很多,觉得非常棒。可能很多人从2000年以后就不听摇滚乐了,他就一直认为摇滚乐在走下坡路,其实不是摇滚乐在走下坡路,而是你离摇滚乐很远了。摇滚乐本来就是年轻人创造的,它也始终属于年轻人这个群体,如果说它没有像以前那样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那是因为它回到了正确的地方。它从来就不是大众和主流文化,在一个成熟的分众化社会里,摇滚乐迷永远只占人群的百分之五到十,这才是正常的。”
因此高旗认为,中国摇滚现在的状态非常好。“乐队通过演出、通过歌迷的支持就可以养活自己,还有能力做自己最想做的音乐,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这就是我们在90年代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90年代那会儿做不到。”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状态也非常好。“我现在也还挺年轻的啊,我还有很多很多新的音乐要出来,还有七八张到十张专辑要出,有上百首歌给大家,还会有很多的巡演。这都是以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只是需要时间,我都会慢慢地去实现。”
以上文字来自北京青年报电子版,文/崔巍,原标题:从重金属到童声合唱高旗的两面:玩摇滚和玩宋词
架势堂(casstop.com) —— “有摇滚,好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