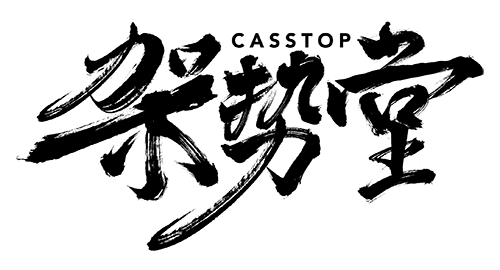在周云蓬因自己的第三张唱片《中国孩子》一蹴而红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在酒桌上对自己“音乐公民”、“抗议歌手”的处境表示过不安,乃至自嘲,他近日推出的几乎全部以古诗词做为歌词的新唱片《牛羊下山》证明了,他那时的不安和自嘲并非做作。我还记得,《中国孩子》刚流行网络时,诸多平时不怎么听音乐,却总盼望着从音乐里抠出些道义正气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兴奋,简直像半路上捡到一锭大元宝似的,他们忙不迭把这位长发敦实的盲人歌手披挂成时代的斗士,安排在时代的浪尖上,然后躲在后面叨逼叨。
对于“公民”、“抗议”、“斗士”、“浪尖”这些词,周云蓬即使喜爱,却也一定没有爱到要把它们涂上金粉、挂于门楣的程度,何况别说眼盲心明的他,连我都嗅到了这里面有一种逼迫的味道。如此说来,《牛羊下山》对政治、当下、现实主义的刻意规避,可看作是周云蓬对那些期望他在新作品里更犀利、更尖锐、更猛烈的人一种刻意的辜负,看着那些帮闲者失望的脸,别说眼盲心明的他,连我都禁不住心里一荡。
当然,不会有艺术家单纯地仅冲着令人失望来进行创作的,除非这样做能令他的价值系统散发光辉、美学观点得到展示。与《中国孩子》里的草根态度、社会批判相比,《牛羊下山》里的风花雪月、思古幽情显然离周云蓬的美学根本更近。一边听这张唱片,一边读他发表在《独唱团》上的散文《绿皮火车》,你会明白在今日中国一个正宗的、典型的、毫无瑕疵的文艺青年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没错,就是周云蓬这副模样。在今天说谁是文艺青年有些像骂人,这个怪像,由一些本来就算不是很好至少也算正常的词汇被滥用、乱用、喷饭用而导致,这些词包括文艺青年和女文艺青年,包括菊花和芙蓉,包括劈柴喂马和劈马喂柴——为什么不能让这些词像周云蓬一般,坐回自己本来的位置呢?
架势堂(casstop.com) —— “有摇滚,好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