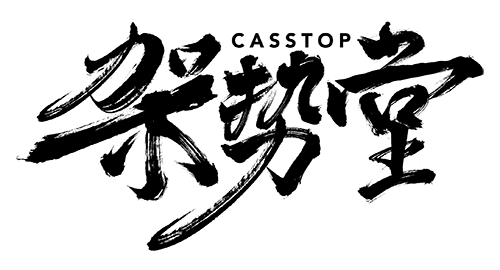1、重金属
一切从唐朝开始。
1992年底的《梦回唐朝》,成就了大陆独立音乐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神话时代。尤其被“滚石·中国火”刻意神话为“亚洲最伟大吉他手”的刘义君(老五),曾经练琴的刻苦、生活的艰难窘迫,更激励了大批热血青年拿起吉他积极投身其中。
但事实上,轰轰烈烈的重金属狂潮并没有铸造出哪怕一支能够和唐朝相提并论的组合。虚假繁荣之后,留给大陆独立音乐史的只是几张头发同样披散的伪金属专辑。但我并不怀疑那些人们曾经的热情,只是《梦回唐朝》所树立起的标杆过于高大。而这也包括唐朝本身。相比《梦回唐朝》,无论是编配、词曲还是整体制作,《演义》已不是拙劣二字所能诠释。关于此,似乎正好佐证了《梦回唐朝》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根本不是出自唐朝之手的传言。只是,我更愿意相信那是被榨干了所有灵感的结果。毕竟,我没有亲见。至于那个“张炬的死对唐朝到底产生多大影响”的争论,除了唐朝自己,别人都只能是妄加猜测。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张炬在唐朝扮演过的究竟是怎样一种角色。
重金属风潮真正成就的,是如今仗琴行于江湖的那些被称为吉他英雄的音乐家。李延亮、歇斯、汶麟、陈磊…,无一不是从金属开始。在网络,总有类似“谁是中国最好的吉他手的争论”,而事实上,任何人和事都是相对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不同观点也就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缺陷,这不可避免。关键是这个圈子的和谐、共进。我看见过对吉他音乐戴上有色眼镜的狭隘批评,除了一笑了之,真的想不出还能做些什么。如果那是一种炫耀,是没有灵魂缺少情感的污七八糟,那么,纯音乐表述的电子、先锋、噪音的价值又何在?
而那些因重金属风潮也揭竿而起苦练琴技并彻底优秀过,但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掩埋起年少冲动的更多人,就真的成为一种悲剧。他们的舞台,已从当年的影剧院换到了私立音乐学校、舞厅或哪家开张大吉的商场门口,融在庸碌的人群,靠多年打下的牢固技术根底在纷乱中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带出了几乎所有城市新生的技术高手,把压箱底的功夫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一定会不断涌现下去的新一代。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憧憬过自己的学生能够完成他们也有过的梦想,但在很多人毕恭毕敬的一声“老师”里,我能够体会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动。而在偶忆起自己血气方刚时对技艺的不懈追求,那发自内心的对如今孩子们拈轻怕重的感叹,又该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从未停止过的想往?!
2、朋克(流行朋克)
至今,我仍没有搞清楚“PUNK”这个词在中国自诩朋克者的内心里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很多时候,我愿意把朋克当成是一种精神。对我来说,这种观念的形成,源于所有能够接触和涉及到的关于欧美国家“朋克自由”的推介。那是一种多么的美好,想往神圣。可是,轮及我们真正面对的,却是一种完全变了味道的孳生物。
我能够记起几年以前高举“技术时代已过去了”的幡子,置亲生父母教给的天地良心于不顾,狂舔可能为其带去一己私利的谁谁谁屁眼儿的那位杂碎。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个人企图,但因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朋克在中国,是害怕刻苦练琴又贪图名利者的幌子,“技术无用”“三个和弦”是硬造给中国小朋们赖以起家的资本。在还没有弄清和弦根音为何物的时候,跺脚甩臀摇头摆尾的功夫就已炉火纯青,对舞台动作的钻研是他们之中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好像,就从没有注意过一直被他们奉若神明的Kurt同志的那首《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的编配,可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弹出味道的东西啊!朋克在中国,是“没钱花了回家去要没饭吃了回家去吃”的北京中产阶级襁褓子女们的业余消遣,他们不必发愁没有趁手的名牌琴和高级效果器、不必发愁生存和生活,唯一能够使他们辗转反侧的是开着私家车欺骗了多少少女贞操,博得了多少其实低贱的“美”名。朋克在中国,是市井街头下三滥小混混们闲来无事哗众取宠的工具,他们善于抓住女人的虚荣心理,不失时机的摆酷和装B,弄出一副性感撩人的伪善模样留连于美色和更换女人。朋克在中国,是哪些庸才投奸取巧的出路,猪头猪脑做不出正儿八经的音乐,就顺手拈来“朋克”二字,穿上奇装、戴上狗链、随口骂娘和滥交,装出一副形式主义PUNK的大致架式。朋克在中国,是整日无所事事吊儿郎当的借口、是炮眼儿女人们的阶梯、是摇滚江湖赤脚游医和半仙儿们赖以活命的药箱和招魂幡!
真的,我害怕提及Made In Beijing China的Pop-Punk这个绝对的屈辱字眼。它是中国独立音乐的奇耻大辱,是绝对可以升华为整个世界音乐史的丑闻,是无知才会无畏的音乐败类们的踮脚石,是连说话大舌头都可以被粉饰为优点者欺名盗世的本钱,是撑起摇滚臭虫们自尊的脊梁骨……我承认,我曾为某乐队宣传文案里所提及的“入世哲学、人文精神、世界观”等字眼感动。但翻开封页看了“我只能爱你到天亮、我知道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如果我需要你的爱我会随时叫你来……”之类的宣言,我终于相信,就算是孔子他老人家,也肯定预料不到几千年后的中国竟有人愚蠢到如此恬不知耻的地步!而那几个连歌词和声都要制作人帮忙编写、老大不小了还妄称“未成年人”的小朋,是不是还在酝酿新唱片上市之后要通过媒介宣扬已发现多少万盘儿盗版,以给那比万里长城的城墙都要厚实的脸皮再贴上一层屎黄色呢?
你当然知道那群依旧自诩无聊的跳梁小丑。用嘴佯装出一副世事无常激进叛逆的嘴脸,张口闭口的“操你妈”“傻逼”和“你丫”。真的,到你有种跟你爹妈老祖宗说话也这样的时候、到你不需要对洋婆子出卖色相换取药品和快感的时候、到你能够放下发自骨子深处的卑贱和劣根意识的时候,我能够真心的为你叫好和暴跳,然后认同你拿手的招摇撞骗!而那个高喊过外地乐队都是农民、经常被自己人喊了倒好还傻B呵呵欣喜异常、高唱着爱恨情仇染成绿毛儿就自以为PUNK了的乐队,如今还残存有能够让人提起和记忆的资本吗?至于某女人曾经那让世人笑掉大牙笑破肚皮的、类似“不做音乐就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可能就会死的”回答,除了中国自诩朋克者的绝对装逼典范资格,还有什么?
但如此种种,我的思路却又常被诸位Pop-Punk大师们,动不动就宣扬的要去或已经去了某国巡演的骄傲打断。中国独立音乐,甚至包括崔健、爻释·子曰、超载等,尚没有机会到别国多个城市巡演的情况下,是这些天才的Pop-Punk腕儿毅然决然的挑起了万斤重担。但是,已经发生过的多么“声势浩大”的大师的艺术路程,居然没有上央视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可能也正是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悲剧”之所在吧。
如果还能够称得上是一场接近朋克本质的运动,应该是从盘古开始。那个时候,《猪三部曲·圈》也正被赋予着一种神秘,宛如盘古生命的唯一精品,在各式不同的录音机上被传遍大江南北。其主唱站在大众视角所直抒出的愤怒是原始和真实的,他在他能够理解的层面上努力表达出的带给着听者足够的震撼。在我意识里,除了盘古,中国式朋克的真正明星,还有《垃圾场》的何勇,其次是太原的“隐患”。虽然隐患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站到这个舞台,但我知道那个名叫白军的年轻人,也同样善于思索且目光敏锐。在中国,彻底朋克是社会底层人民的原始愤怒和冲动,是世道不公和失业激增的双重产物,是读不起书上不起学的后遗症,是养不起家看不起病的无奈抗争……虽然它永远达不到欧美朋克者们对政权和国家肮脏毫无顾忌的指责和对乱交毒品从不回避的高度,但至少,在我们的体制下,它能够成为一种发泄的工具,即使永远摧残不了什么。
一九九九年,上海扩音器乐队的Demo专辑带给过我短暂的兴奋,不知道如今的他们是否依旧Punk。而曾经的武汉朋克暴力团,呵呵,我想就算了吧。相比较,我更认可当年身边“繁殖”那诚实的冲动,没有狡诈和慌蛮。还有已远去的三个矿工儿子的组合“曲别针”,五年以前的凌乱现场依旧深印在我脑海。主唱浓厚哥特嗓音下《我的思想被狗吃了》和《与魔鬼战斗的人》的莽撞,依旧让我感动……
更多时候,我不愿意把Punk这个词看成一种单纯的音乐风格。它代表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彻骨的争斗和针锋相对。而且,Punk并不一定就是抨击和批判,就像江西景德镇的原子弹乐队那句著名的“强奸东京三十万活埋东京三十万”一样,它同样可以升华为伟大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觉悟。而我们又怎能拒绝九六年深秋的北京南站,我见到的那位为父上访伸冤已二十载的老人,在收拾被囊迈出蹒跚但绝对坚毅的脚步之前所说的那句话: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告下去!
Punk,并不是用嘴巴就能够随便说出来的东西。它更深远的意义,是推动你不断做下去、坚持下去的力量。
永远,永远…
3、重型说唱
这是我真的想满怀崇敬开始的主题,因为那开创了中国独立音乐新格局的一群人。而冥冥中,“重说”这个如今和“Punk”几乎已同样烂俗的词,又真的让我不知所措。
几年以前的电话里,那个操浓浓湖南方言的家伙带给我两个全新的名字:痛苦的信仰、扭曲的机器。说实话,当时听来只是好奇,中国大陆很少有过这么长名字的乐队。而那个时候的“重说”,尚能够把持住纯洁,没有风起云涌,更没有泛滥成灾。但随时间推移,大陆独立音乐继Made In China的Pop-Punk耻辱史之后,再次落入的蹩脚重说狂潮,又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另外一种“力量”的魅力。
而这种“力量”的最直接体现,是重说乐队占绝对主角并且依旧层出不穷、如今已举办了四届的北京迷迪音乐节。那庞大的号召力、触角,让更多酷似愤怒、好吃懒做的年轻人,在看到活生生摆在眼前的“明星”标本之后,也找到属于自己发泄和装B的途径。我从来都不相信,中国有那么多的重说乐队具备发唱片的水准。这和当年倍受批评的灵感、佤族等老摇滚,有异曲同工之美。只是,随时代的发展,如今的重说更知道且方便和圈内媒体搞好关系,而封住了很多张嘴巴。
重说是什么?体力充沛当然是必需的,把不知哪位老祖宗研制的标准“重说演出动作”琢磨透、模仿像也是必需的,主唱故意低沉且底气充足够劲的嗓音更是必需的。但不能如此就万事大吉,音乐毕竟是音乐,要讲究编配和技法。演奏前在潜意识里就先摆好了准备POGO的姿势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只是江湖骗子的鬼把戏。可即便如此,那些本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们,仍在磨刀霍霍准备投身其中,为什么?
有些人是知道这样一个典故的:某重说乐队的现场,吉他手头晃晕了、腰蹦闪了、汗把衣服打透了。可明眼人却发现,数首歌的整整一场演出下来,此君居然只用了一个E和弦。故此得名为“一E到底”。面对这事实上的莫大嘲讽,引领了中国重说风潮的大腕儿们,你该做何感想?
我看过中国所有著名重说乐队的演出,且不止一次。但我对重说一直不太感兴趣,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而这并不冲突,毕竟,大家都是存在于中国独立音乐这个圈子。它的荣辱与否,才是我们切实关心和在意的。2003年迷迪音乐节,那些熟透甚至已发了第二张唱片的老面孔,依旧躺在光阴上自我满足,唱着过去时的“成名句”,凭空的愤怒和咒骂政治。而任何一种音乐,辉煌、高潮之后理所当然的突破和创新,无从寻觅。所以,我曾经说过,中国的重型说唱只留下一个“痛仰”就足够了。这是显得偏激,但在重说那条脚印早已杂乱无章的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至少“痛仰”在大胆尝试音乐的改变。
不管怎样,重说依旧风行,新人依旧涌现。只是,中国“重型说唱”的出路究竟如何,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4、低调
低调音乐没有像Punk、重说那样掀起一时风潮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对个人技艺要求的严谨,及作品相对内敛阻碍住“激情澎湃”的表达。不可否认,更多人对Punk、重说的喜爱甚至也加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简单直接的热闹成就的一时快感。他们不会在乎乐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即使他们也一样附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没人会给你面子”的精彩,并且群情激昂,也遮掩不住实质上的“票友”本质。迷迪现场,面对低调乐队演出时那只是偶尔随声附和的绵软无力的手,大多人选择的呆望和沉默,及少数的不耐烦举动,让我心生感慨。盲从的一代,随波逐流,甚至就没有想过应该追寻的目标。他们怀揣父母的血汗钱,长途跋涉,或者毫不犹豫买下的专场大面额门票,为的,或许只是一种名头、一种热闹非凡、一个免费观赏“名人”聚集的机会。来过、闹过,然后,过眼云烟。
很多人喜欢把低调音乐的开始定义为木马,但木马的气质更接近于哥特。那催人泪下的唯美,曾让我为之一震。而相对于木马堪称宏大的背景音乐及吉他效果,废墟创造的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美,简洁、纯粹、干净,时而又制造迷幻。我知道很多人是乐衷于主唱周云山的凄厉尖叫,而这个闲坐下来就喜欢憧憬和幻想的家伙,更多时候留给人的却是一个沉默的诗话表象及歌词。声音碎片是已经发了专辑的,实力自不必说。但遗憾的是,长久以来,他们仍未能摆脱Rediohead的束缚。星期三旅行多灾多难,在向成熟转型的关键阶段,鼓手毛豆退出。他们已经发了七首单曲,但专辑仍没有着落。我看过的新加了一把吉他后的演出,音乐更加充实,在或舒缓或躁动中,萦造着一种阴暗的美。只是,他们的全英文歌词,限制着与观众更直接的交流。
在这个需要器乐和嗓子制造高潮的音乐形式,似乎,更多需要的是理性的音乐人和更加理智的观众。
5、电子·实验·先锋
电子是新时代的科技产物,是需要昂贵设备支撑起脊梁的奢侈品。所以,它应该是只属于有钱人的游戏。但我们确实接触的,是更多“在现有简陋设备制作最精彩音乐”的人们。
早在一九九一年开始研学电脑音乐的王勇,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举办的“首届中国MIDI作品比赛”上,就凭一首名为《喜马拉雅》的作品摘得二等奖。而他于一九九六年在魔岩旗下发行的专辑《往生》,则应该是大陆独立音乐历程上的第一张带有浓厚电子采样色彩的唱片。
事实上,电子乐在很多情况下是和先锋、实验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都是一种尝试和摸索。
王凡和王磊是当仁不让的先行者,只不过相比王磊的“龙民录音棚”及周边设备,如今的王凡也还只有一台RoLand VS880型号的八轨机。但就是如此的简陋设备,却出产了《身体里的冥响》《五行》《诗歌》等传世佳作。王磊的早期唱片,基本都是在现成乐器上的实践,直到《美丽城》才彻显电子本色(《王磊&泵》我没有听过)。而大地唱片于九五年推出的金武林《严肃音乐·失落园》,在多年以后,才成为很多人怀念和评写的资本。
丰江舟已俨然一代宗师,这个一直被生活教育着的人,从苍蝇开始就树立了其卓然不群的音乐形象。在方无行的《另类拼盘》及青山工作室的一张合辑里,分别发行过苍蝇的单曲。他曾与毛豆合作过一场电子乐演出,并在2002年的迷迪音乐节靠一个笔记本征服听众。毛豆的《粉》,开始的则是毛豆自己的新时代,让他更专注于一个人的音乐。并和郭大纲、丰江舟一起,在直接流行的《电核噪动一》发表单曲。
另外还有不少可以记录的名字,比如张亚东。只是,他更多的生活在流行界。卢小旭则在游戏配乐界叱咤风云。
电子、实验、先锋,拓宽了更多音乐家的艺术路程。但也让分散在以上海等地为代表的庸才们有了欺世盗名的机会,并且一不留神就被亲戚朋友捧上天,最次也自己印上几张DEMO聊以自慰。
但幸好,这个同样被利用着的音乐形式,尚没有形成彻底变味儿的大规模风潮。只是,那还会远吗?
6、校园民谣
这是整整一代人青春的印迹。曾经,我们一样迷茫、懵懂,初涉人世。在学生时代的结尾,“校园民谣”悄无声息的就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像出现在几张唱片里已青春不再的每个歌手一样,我们伤感、朦胧。
当年大地唱片公司肯定也没有想到,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制作宣传,因为“青春、伤感”这两个绝对的悲剧字眼,成就了一个时代。
和“校园民谣”联系最为紧密的名字,应该属于高晓松。这位靠《同桌的你》功成名就的作者,后来又写了《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冬季校园》等几首脍炙人口的歌,即便他的旋律很多都能够听出罗大佑的影子。另外必须提及的两个人是沈庆和郁冬,所有这些靠校园民谣混上饭吃的人,都是紧紧抓住了“梦想、爱情”这两个对于走出校门、青春已逝的人的悲剧主题。
电脑里正响起《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儿,并没有感觉什么。可是,九年之后的今天,我禁不住唏嘘。只有真的走出校门,荣耀过、挫折过,才能够体会灵魂深处的那种沉淀、积聚。那是真的能够让人流泪的感觉,即便一切都在遥远着、苍茫……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尤其记忆。
事实上,“校园民谣”最关键的还是女人。即使是梦想,也都无一例外的寄托着,那才是深刻在每个人内心里的东西。开始一场爱情,其实就是开始一场自己明知道会以悲剧收尾的戏。更何况真的悲痛欲绝的初恋呢?!前些天,偶听到有人哼着我学生时代的作品《鲜花》,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写给我初恋的,记录了自己莽撞过的青春。我知道是当年三千多人的现场,让它流传了,即使不能永久。恍然间,我也就真的明白,“校园民谣”最重要的意义,是怀念。青春、梦想、初恋、女人,所以伤感、所以悲剧,即使遥远。而这,才是再也找寻不到的纯洁感情。
如今的大学生,大都在丧失理性的疯狂膜拜。“校园民谣”对于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字眼。他们需要的,除了诸如F4、韩流之类的娱乐,就只剩下生理的冲动和渴求,以及网络可能带给他们一夜情之后的虚无。没有梦想,没有。所以,他们听不到那个时代的歌儿,听不到感动。
架势堂(casstop.com) —— “有摇滚,好架势!”